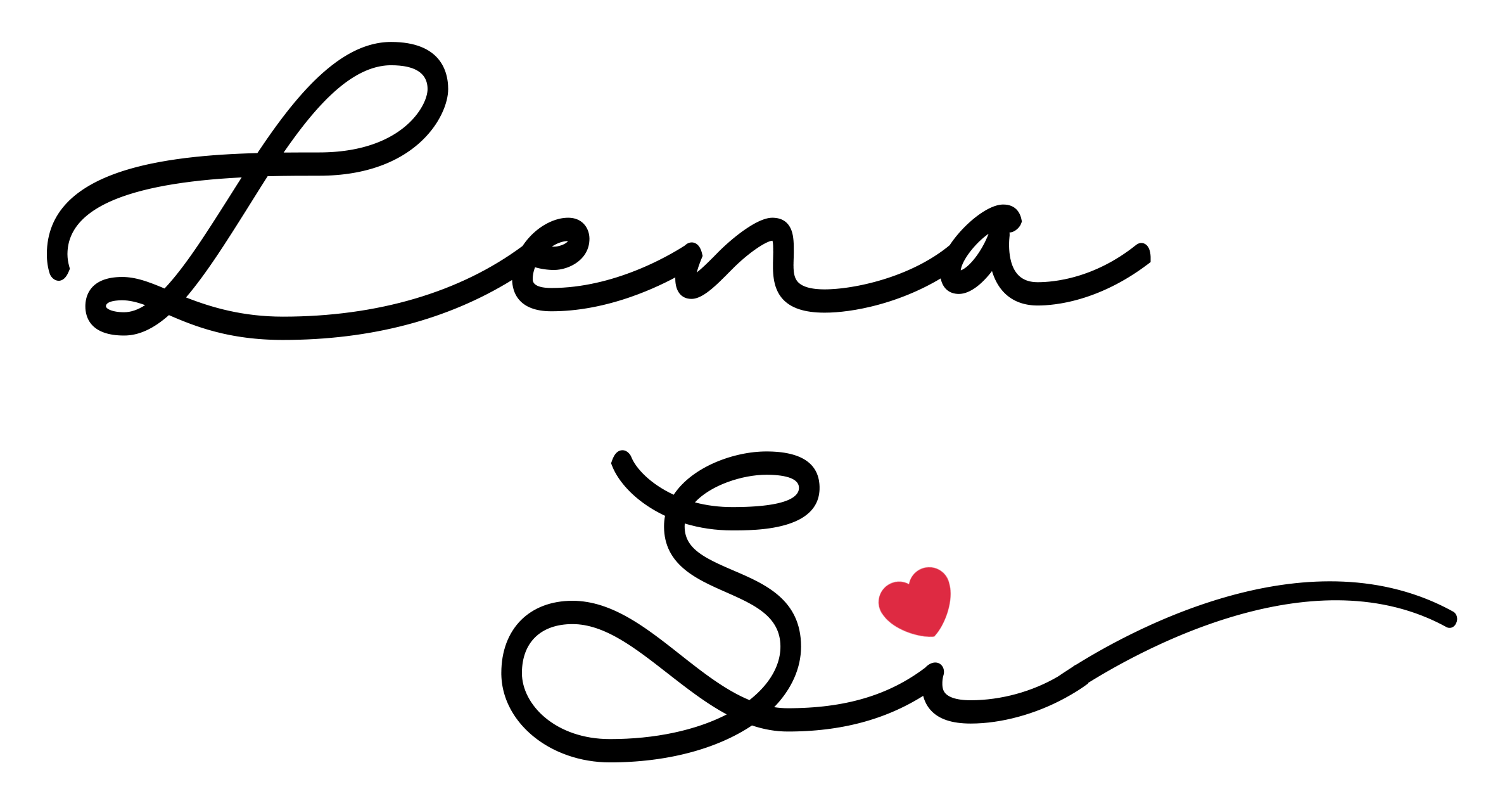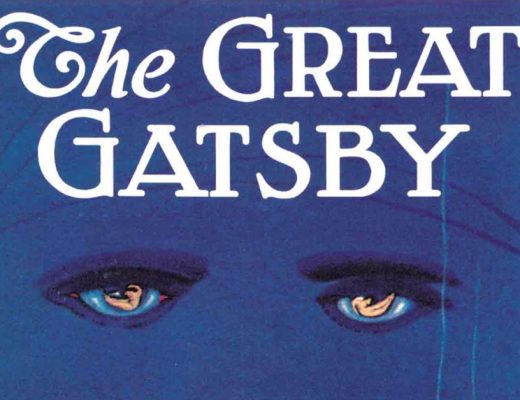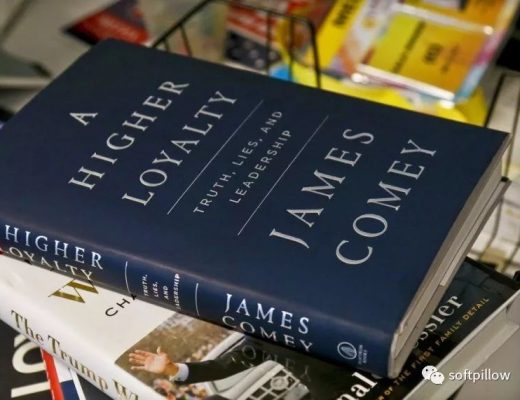偶然间看到老同学照的北京星空,猎户座清晰可见,有一种无比熟悉的感觉,毕竟在很长时间里,我只认识这一个星座。
在我年幼的时候,妈妈试图培养我对科学的热爱,带我去了天文馆,整整一天只有一幕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,就是在穹幕电影院里,有一个类似赵忠祥的男声解说介绍,每当到了冬天,北方天空上最显著的就是猎户座,三颗连排星座是猎人的腰带。我觉得三颗连成一排是很酷的事儿,就低头看了下星座示意图,怎知从此猎户座就成为了我唯一认识的星座。冬天的晚上走在路上,都会抬头看下猎户座,潜意识里说一句,哦,他又在那里,然后脑中又会想起“北方天空”的解说……
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对宇宙充满好奇,仿佛宇宙便是人类最高级的追求,然而我却一直很惧怕宇宙。我不想上太空,不想知道宇宙怎么来的,会变成什么样,不想知道宇宙外面有什么。大一的时候,理学院要求我们必须上一门物理,要不是普通物理,要不是天文,我去试了一次天文课,做了一次作业,就有种明天地球就要被吸进黑洞的恐慌,落荒而逃。
我从小就有种脑洞大开的信念,笃定宇宙外面就是佛在的地方,我们这些星球就像如来掌心的孙悟空,佛没事就随便拨弄拨弄(大概《Men In Black》系列的片尾比较贴近我的宇宙观)。学天文会让我有种信仰破灭的恐慌,所以我似乎有意在避免,我宁肯把星空当成一个神奇的充满故事的浪漫之地,远远看看就好。
然而我是个大近视眼,所以平日城里实在是看不见什么星星。偶尔有些在野外清清楚楚看星星的机会,我便会记得格外清楚。有一年夏天我们全家开车去南方旅游,旅途劳顿,最后一天赶路回家,凌晨仍然在G4上奔驰。妈妈已经睡着了,为了避免爸爸是唯一清醒的人,我一直在和睡神奋战。后来,看着路前方的夜空,想到是七夕,我打开Starwalk,开始对着手机找牛郎织女星以及天鹅座。这大概是我认的第二个星座吧,当然并不如我喜爱的猎户座那般形象分明,但那晚我就在半梦半醒间和星星打着招呼,直到天色蒙蒙亮。
我看过的最美的星空是在新西兰的Tekapo湖边。那时是南半球的初春,天气还很凉,我们窝在湖边的房车营地里开着暖风过夜。本以为一夜都是阴天看不到星空了,但半夜的时候爸爸叫我起来,说云散开一些,于是我们裹上羽绒服,摸着黑摇摇晃晃穿过凹凸不平长满野草的土地到了湖边。云露出缝隙的时候是神奇的一刻,繁星和银河点亮了夜空,呈现一种画中的深蓝色,我大概是头一次看清这么繁密的星空,原来真的会有一种无法呼吸的感觉。在那种景致下,自己仿佛置身童话魔法中,完美排布的疏密构图,无法想象的颜色渐变,在这种绝对的美中,任何关于星星的传说故事我都会全盘接受。那些兀自闪烁的星星好像真的在诉说远古的故事,太久远所以它们都变得安静起来,太壮烈所以地上的凡人只能景仰赞叹。
其实对于我们来说,星空就是触目能及的永恒,虽然每一刻都在移动,但看起来仍旧美丽宁静,说无常又有常。而星空离我们又那样遥远,若隐若现,让每个人都可以放心地在梦中在心中随意编织自己的星空传奇,似无形又有形。就像向日葵对太阳的崇拜,我们也会本能折服于这种永恒的感觉吧,所以李白才会许下“永结无情游,相期邈云汉”的约定。
快新年了,就暂时远离下俗世纷扰,假装自己在北京和大家一起看星星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