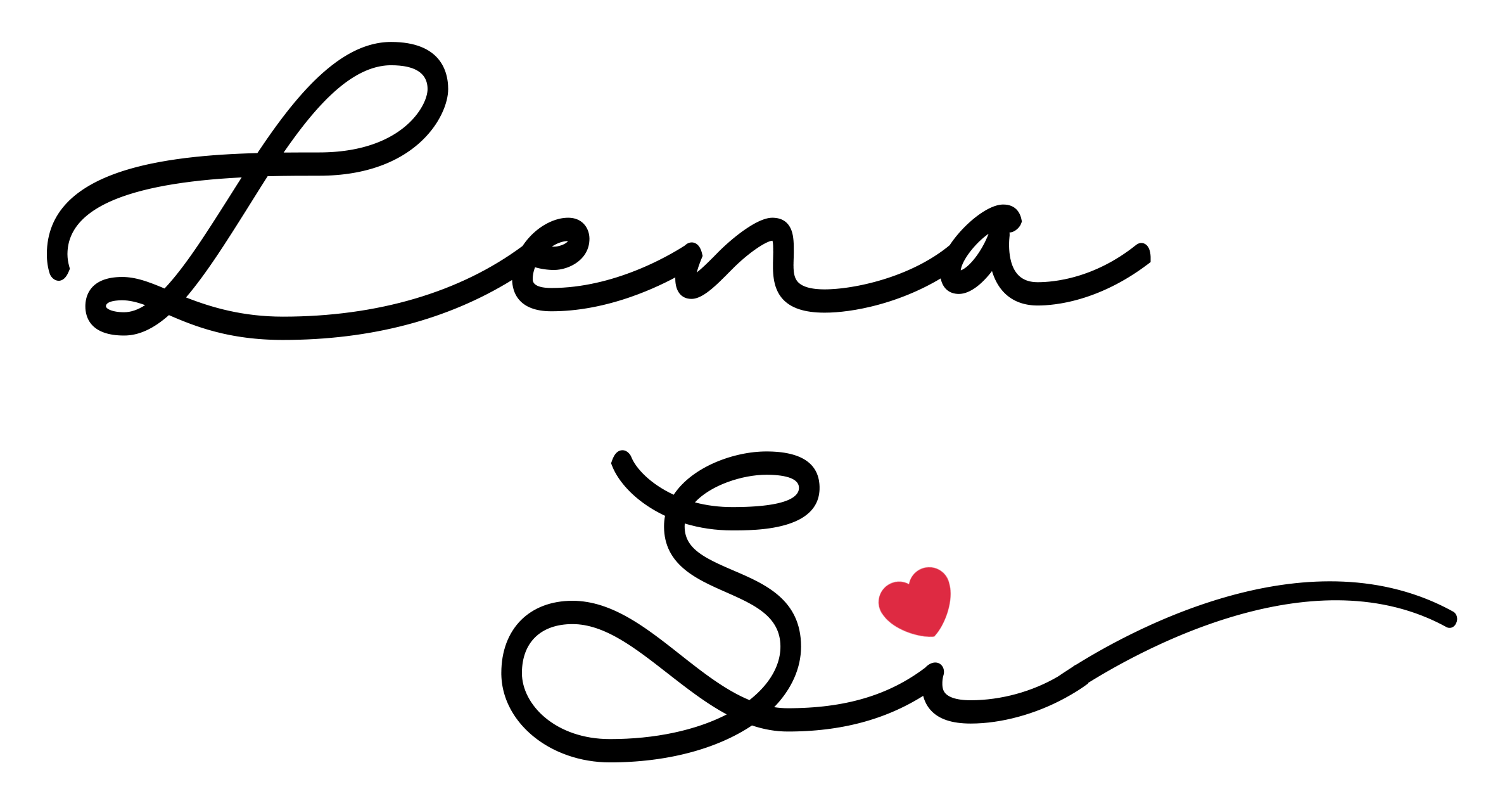一
旅途从租车开始,和所有自驾游一样,我和同伴拿了车,跑去附近的超市采购食水。佛罗里达的天气仿佛是正在缺席的加州,青天白日,热得人只想脱脱脱,我们拎着旅行箱,在狭小的超市洗手间里,换下长裤长袖球鞋,穿上短裤背心拖鞋。虽然仅仅是下了一夜未眠的航班,但毕竟是崭新的一天,颇有态度地洗脸梳头化妆,戴上大耳环,似乎这样,迈阿密的旅程才真正的开始。
但我们已经在睡眠的边缘,强力节奏的hiphop也难以让人保持清醒,尤其是墨镜里稍微暗淡的日光,似乎闭眼才是故乡。纵然如此,我们嘴里仍然喊着好开心,哇,我们在迈阿密了,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。同伴说先去wynwood看壁画吧,结果这里竟然很不错,出照片那种不错。Omar说过,人生就是要把别人羡慕你的地方发扬光大,再甩回别人的脸上。所以拍照大概是旅行最重要的意义之一,拍完照还要发到instagram,发到朋友圈,带上一个坐标才更完美。想不到,最后还是臭美的动力才能让人保持清醒,我们在艳阳下眯着眼睛竟然在这巴掌大的空间里玩了一个多小时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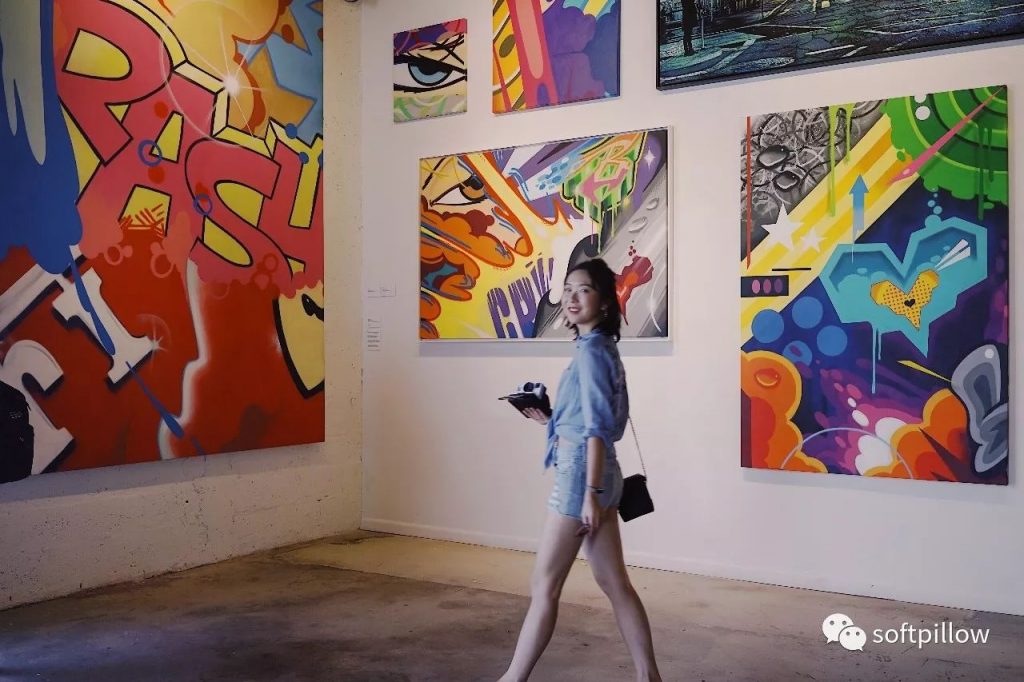

从wynwood出来,已经一点多,但是因为生物钟紊乱,我毫无胃口。同伴早早就查好了迈阿密的古巴餐馆,叫havana 1957,正好也在海边。我看着那一堆炸出来的玉米制品和乱七八糟开胃小食,不禁开始想吃窝头,也是玉米做的,不用炸,还有淡淡的甜味,我便就着想象中的窝头吃完了一桌没什么感觉的古巴“美食”。唯一可圈可点的大概就是芒果mojito,里面插着一段甘蔗,回味甘甜。

完成了同伴的旅行任务,我们溜达到沙滩边,找了一个躺椅,直接瘫了下去。不过想象中的沙滩上睡觉并没有那么美好,一要担心财物,二是太阳躲进云里的那会儿,海风吹着很冷,三是太阳出来了以后又担心戴着墨镜日光浴,醒来脸上会晒出眼镜的痕迹。我把衬衫盖在脸上,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,脑海中不停地想到《你好,忧愁》以及更多的《tender is the night》。那个小演员在海滩上睡着了,醒来以后,海滩上的人都走光了,然后呢?好像他们在一个庄园里吃了一个虚伪的晚餐……就是这样,一直过着小说里的片段,分不清是睡着了还是醒的,似乎还有人来到我们跟前,问我们要不要冰啤酒。
二
第二天,我们按计划去了everglades,湿地中绿意盈盈,随意可见白色鸥鹭,我看到绿色就觉得很美好,觉得远离了加州的枯黄,人生都可爱起来。因为前段时间的飓风,鳄鱼都走的差不多了,我们在anhinga trail转了两圈,只在一个水中竖起来的枯树枝下见到一小段鳄鱼的身影,露出半个脑袋,好像一段平淡无奇的粗糙的木头。

我们的时间来不及驾车去key west,便在key largo的一个海滩上玩了起来,真实的蓝天碧海白沙,虽然不大,但色彩明艳。坐在一个炮台雕塑上,把昨日没晒到的一面对着太阳,和其他晒太阳的人聊聊天,各自都是坐了红眼航班从萧瑟处飞来南方的最南端,在沙滩上无所事事。这样子的放松,似乎上了法学院以后就没再有过了,总是有要做的事情,没完没了的。


“I want a sugar daddy right now, so that I can live like this.”
“You mean, living with old people in Florida?”
同伴作为一个九零后,也是查好了餐馆,在key largo fisheries。海鲜在菜单上看起来很吸引人,只是上了桌真的一言难尽。炸成一团一团的是龙虾肉,也吃不出来和麦乐鸡和鸡米花有什么区别,鱼柳也是裹一裹炸一炸,吃着都是涩涩略微有些老的纤维。crab chowder还算正常,就是没有面包很不满足。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key lime pie了吧,感觉还算清新,可以带走一些油腻感。

从the keys到奥兰多还要开四个小时,天很快就黑了,佛罗里达的高速都收费,相对的车速也就可以高一些。我的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片段,似乎不知不觉笑了出来,同伴在黑暗中问我在笑什么,声音桀桀,我突然有些语塞,有种被抓包的尴尬。“在想一些有趣的朋友,”我支吾道。一个黑暗中的乘客,长路漫漫,为什么还不睡呢,让我一个司机突然失去了一种舒适的自由。
三
难以想象我为什么又来到了迪士尼,我觉得有些抓狂。我比较早熟,在童心面前一直比较无所适从,以为好不容易成人以后可以离开这些在我看来略微不合时宜的活动,没想到还要通过各种活动测试童心,比如万圣节,比如迪士尼。

我看着欢乐的工作人员,突然想,如果有个专杀孩子的连环杀手,这里真是完美的工作场所。于是我开始四处张望,想找到一个可疑的接待员,略微罗锅,鹰钩鼻,他的脸上堆满笑容,可是眼神却很冰冷,你不能只看着那双眼睛。可能他在类似鬼屋的地方工作,可以间歇性半开玩笑式的表达他的愤怒,真真假假,小孩儿从他身前一边笑一边尖叫地跑开。
我们排了一个小时,去玩space mountain过山车,同伴说没有头朝下的部分,我想,能有多难,便大义凛然地上了车。噢,我的天,太久没有玩失重的项目,我大概忘了这是种多么可怕的活动。有个连续俯冲的瞬间,我觉得嘴都张不开了,耳朵突然听不到别的,似乎感官暂时屏蔽了一切。我跟自己说,呼吸啊,于是接下来的行程我一直紧抓着扶手,注意规律呼吸。过山车在一片黑暗之中穿梭旋转,可能有一些宇宙主题,但我闭上眼睛没有看。我在想,有没有紧急制动一类的东西,有没有呼叫系统,我只想赶紧停下来离开这里。当然是不会有的,娱乐项目感觉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,我只能盼着它快完快完。
下了过山车,我的手和腿都在抖,看到系统里的抓拍,紧闭着眼睛张着嘴,脸都变了形,上臂那点肌肉都用来抠着扶手。但是坐在我后面的一个白发老头,一只手搭在扶手上,一只手拨弄胸前的扣子,休闲得很。再后面的小男孩,笑脸盈盈,同样坐得颇为放松。同伴嘲笑我说,一米一以上的儿童都可以坐的,我不听她的,跑去旁边先买了个冰淇淋压压惊。

“I don’t get it. Why are you so scared of rides? You speed like crazy when you drive.”
“It’s all about control.”
我伸手发誓说,今天的过山车到此结束,再也不要坐任何ride了。同伴说好,先歇会儿,然后各自跑去买了一个火鸡腿,那东西油腻得很,吃完又要买杯可乐解解腻,这样晃到了下午三点多,同伴又软磨硬泡我去玩矿山小火车。我们排了不知道有多久,我在写日记,她在看reading,我们都尝试过得有效率一点。但是上了矿山小火车那一刻我又后悔了,我想起高中毕业在欢乐谷,我从激流勇进的船里路过,逃兵一样从另一侧离开了现场,留下一脸懵逼的同学。不过这次我还是忍住了从另外一侧下车的冲动,更何况同伴其实先上了车,挡住了我去出口的路。矿山小火车倒确实没有space mountain那么夸张,但我全程在问我同伴,完了没有,完了没有,同伴不胜其扰。
天渐渐黑了下来,同伴继续排队去玩另外一个项目,打死也不要再上任何小火车的我,满迪士尼去找甜的爆米花。爆米花的甜咸之争于美国人大概和豆腐脑的甜咸是一个级别吧。迪士尼城堡的灯亮了起来,我看看表,距离烟火表演还有三个多小时,不禁绝望起来。我套上写着enfant terrible的外套,和同伴说,快照个相,表达一下我的态度。

“What’s your favourite Disney movie?”
“How to train your dragon.”
“That’s not even Disney.”
“Oh, Marvel then.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