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 Chopin Programme
Funeral March in C Minor
Contredanse in G Flat Major
Cantabile in B Flat Major
Souvenir de Paganini in A Major
Nocturne in C Sharp Minor, 1830
Four Mazurkas, Op. 17
Six Etudes from Op. 10Barcarolle in F Sharp Major, Op.59
Three Mazurkas, Op. 59
Two Nocturnes, Op. 62
Polonaise Fantasie, Op. 61Berceuse, Op. 57
Mazurka in F Minor, Op. 68/4
对于傅老的音乐会,我翘首以待了一个月,怎知当天身体不舒服,但仍然忍着奔去了中环大会堂。傅聪1934年生,如今已经76高龄,走过舞台的姿态和波利尼颇为类似,身体前倾,上身驼着,让头更是向前,远远看上去很是瘦小,黑色的褂子,油亮的头发,仿佛是个上了年纪的学究走上台,貌不惊人,却从容自然。
上半场的前几首我想恐怕没有几个人听过录音,更不要说现场了,我也只是弹船歌的时候发现了那首葬礼进行曲,随便玩了两次。听音乐会的心境大约有三种,意料之中,出乎意料和措手不及。意料之中是说从曲子到表演者的诠释手法都是烂熟于新,毫无惊喜可言;出乎意料自是说表演者的处理令人惊叹。而最后一种就是完全连曲子都没有听说过,那便是单纯的公平的音乐欣赏了。我想用葬礼进行曲开始几首遗作的表演,也应该是扣了纪念萧邦的主题。葬礼进行曲弹得非常好,如今古典音乐的录音多得让人都不知道怎么自己理解了,而真正人和人的风格就区别在这里。我想傅聪的强项应该就在乐曲的把握和音色的变幻。后面几首旋律优美,而到夜曲的时候我觉得身上的不舒服已经完全好了。
那首夜曲遗作弹得非常动人,音色饱满,感情强烈,非常钦佩傅聪的音色,浑厚而立体,旋律也都抻得恰到好处。有很多人录的夜曲都不包括这首,我觉得很可惜。玛祖卡永远是音乐会中的出乎意料,曾经有段时间整天听各位大家弹的玛祖卡,当然也包括傅聪本人年轻时的录音,但每次在现场都有似曾相识却不尽相同的感觉。即使傅聪是我听得第一个版本,但仍然他的演奏和录音大相径庭,这便生出一种趣味来,你知道旋律的走向,却不知道某个音他会弹多久,什么时候弹,胃口就这样吊着,吊得心甘情愿。六首练习曲,从第六首开始到第十二首革命,除去第八首。练习曲弹得并不快,磕磕绊绊的地方也不少,这反而引起我中场休息时很多思考。
就拿革命来说,我想音乐会现场就绝对有观众可以弹得比傅聪更快更流畅,况且傅老的音乐会曲目自然是自己选,那弹练习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。我想以古稀之龄敢表演练习曲本来就是一种勇气,而傅聪弹得极为负责,他并不一味讲究速度,只是尽力把每个音弹好,反观有些年轻的钢琴家,只要速度不要精确,就那样囫囵吞枣一通,观众听着爽,可对作品和作曲家毫无尊敬可言。而且,练习曲到底要弹到多快呢?记得萧邦书信中有一段,说他无法思考因为李斯特正在弹他的练习曲,他说那是他从没有想象过的演奏。那时候没有录音,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萧邦怎样弹,李斯特怎样弹,但我们都知道李斯特炫技一流,那根据萧邦的话语,他本人想象的练习曲应该并没有那么炫目。再大胆地推论,如今人们技巧越来越强,是不是也已经远远偏离了萧邦的心思呢?
那么如今的年轻人炫技到底为了什么?为了古典音乐的生存么?一个年轻的钢琴家倘若要上台弹革命,那么他会想底下很多观众也会弹,更何况大多数人都搞不懂音色啊,理解啊是怎么回事,那么他要想让观众佩服他,他就要弹得快,比观众能弹的快,比观众听过的快,这样观众赞叹一声“好快”便心满意足,而他的目的也达到了。记得拉丁舞舞王Donnie Burns曾经在讲习时说,只有跳得不好的体育舞蹈才是体育。我想这话可以用在如今的古典乐坛,只有弹得不够美的表演家才是技术派。这么想来,在台上以再平常不过的速度弹出一场声势浩大却仔细的革命,需要一种怎样的荣辱不惊,恐怕也只有从容的老人们可以做到了。
如果说上半场还有一丝怀疑,下半场就是彻底的景仰。那首船歌弹得美丽极了。到现在为止我听的录音,包括我自己弹的时候,都力求身临其境在一场威尼斯的水上盛宴之中,觥筹交错,舞步轻盈。但傅聪的船歌却是温暖而美好的回忆,就像《追忆似水年华》里普鲁斯特念念不忘的小玛德兰点心,不慌不忙地在意大利的记忆中徜徉。玛祖卡自然不必说,继续吊着胃口,但我忽然想象自己弹琴是否能够这样晃悠一下,却怎么想都觉得滑稽。可能差距就在于,我没有那种可以深刻理解作品的自信,所以就会底气不足,想慢也慢不下来,因为慢意味着更挑剔更细微的审视。让我更加赞叹的是E大调夜曲,从40小节开始音色交织得密密麻麻,排山倒海一般涌来,让我觉得任何书面语言在这般立体的色彩面前都变得苍白,相比之下,大多数其他人表演的夜曲都显得单薄起来,变成一个纸美人。我不禁想到《傅雷家书》里父子二人的对话,恐怕因为傅雷先生对音色的重视才有了傅聪对音色出色的控制。至于最后的幻想波兰舞曲,倒是个意料之外。我听这首曲子很多次了,现场也有很多次,但这是第一次我觉得她非常好听,这大概跟傅聪的速度有很大关系。从中场休息的思考继续说,乐曲要走进人内心是需要一种共振的,总要与某种生命的频率呼应,或许是呼吸的频率,或许是心跳的频率。如今人弹琴越来越快,可呼吸和心跳也不至于比一百年前快很多,这也许是为什么很多表演像走马灯一样耳朵里跑个过场就没了,而傅聪慢斯条理的叙说却可以渗入人心。
其实傅聪在弹船歌到80小节的时候,我就在想他弹摇篮曲一定很好听,而在加演的时候老人真的弹了摇篮曲,前奏响起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,然后就在这种高昂的情绪下听到了最完美的一首摇篮曲。变幻莫测的音色带来了极富歌唱性的表达,美得让人屏气凝神,生怕坏了一场迷离的美梦。我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对这首摇篮曲喟叹不已。曾经看过一篇报道,说傅聪是天赋不够却异常努力的钢琴家,他确实异常努力,但说他天赋不够的人真应该来听听他的摇篮曲,他的船歌,他的夜曲。
随着这场音乐会的落幕,我想这美好的一年也算过去了。而有多少Virtuoso最终可以变成Maestro?还是Maestro的时代也已经快消逝了呢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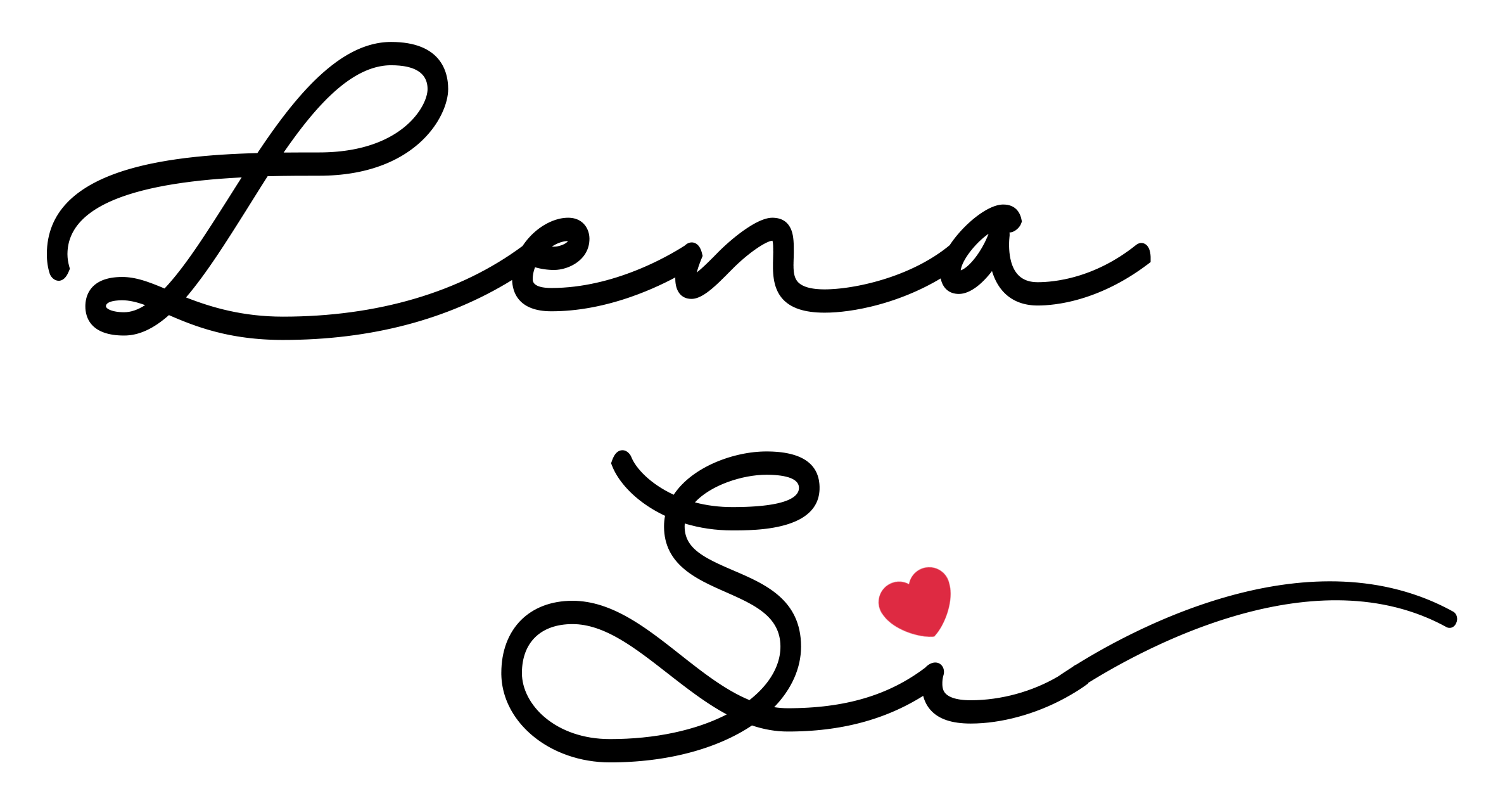



这篇写得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