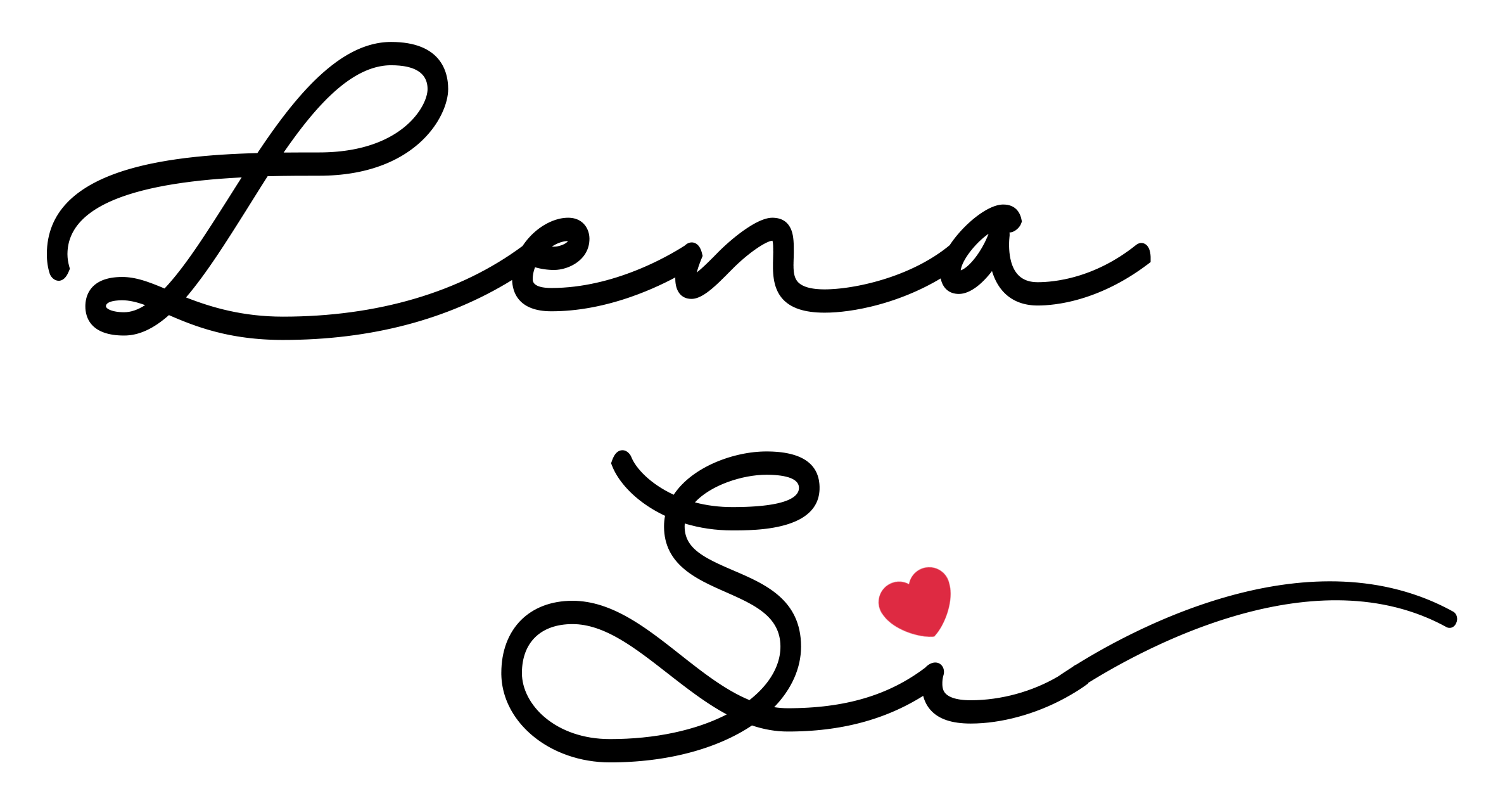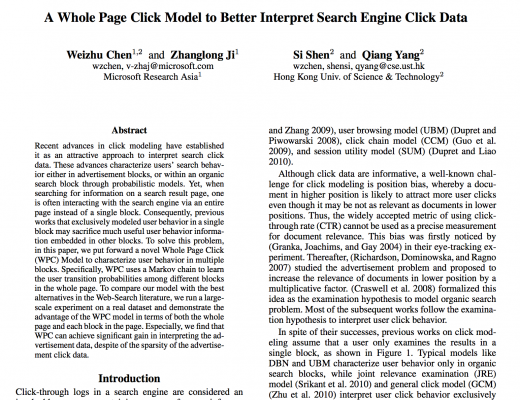整理文件的时候翻出来,作于2010年3月18日。看来当年是准备好好写一写的,但我每次专心坐下来想写东西的时候,只能坚持出5000字,所以你看,后面经常有些语句就像故事大纲。现在早就没有了当时的烦躁,再扩写也不大现实了,何况找补自己的东西最费精力。
——题记
经济不好的时候,没人会想起“人文关怀”这个词。本来贺萧觉得只有资本家才这么没心没肺,不过时间久了也发觉这只是个广告虚词,跟市场没关系。要在北京凑合活着,就什么都不能当真。
本来只是四月一个普通的星期五。若非要说特别,也就是车牌号尾号是“9”的车赶上限行,因此贺萧从父母那里挖来的旧车只能挤在楼下的自行车堆里歇着,横竖都是破铜烂铁,倒也和谐。不过上班路线总变不了,约好的出租车从北五环一路冲锋陷阵到国贸,开车师傅心情烦躁,嘴里咒骂连连。贺萧瘫在后坐懒得搭理,心里只惦记着要早点下班,周五车多,不要堵一个晚上。
他倒是没想到自己中午就顶着艳阳天出了国贸。经理是笑面虎一个,罗罗嗦嗦说了半个钟头才放他出来,安全原因,什么都不许带,直接拿包走人,就差把保安也请上来护送他了。办公室里的小姑娘们抬头看看,心计一个个都深得很,暗暗担心自己的饭碗,赶紧低头瞎忙活。贺萧哼着曲慢悠悠地溜达回自己位子上收拾,余光就见着孙奇嬉皮笑脸地走过来,捶了一记:“哥们儿,没事吧,别想不开啊。”
“你少幸灾乐祸,我他妈又不是贞洁烈妇,正好回去打点打点,晚上泡妞儿去。”伸手钩上孙奇的脖颈,“诶,要不要一起来,放松一下?”
孙奇扯了扯领带,露出一脸馋像,饿死狗见着肉包子一样,压低嗓子:“行啊,电话联系。”然后对着贺萧眨了下眼睛,转身趾高气昂地走了,闹得他一阵恶心。
叫车回去的时候,贺萧想还好自己是北京人,有车有房吃着父母的老本,自己也不是刚毕业的理想主义愣头青了,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,操,好歹也是学建筑的文艺人,正好一直就看不顺眼国贸这两栋楼。
说来说去也就的士司机待人亲切诚恳,你不爽的时候他跟你一起骂,反正又不是骂他祖宗八代。
“还是干您这行是铁饭碗,被炒了鱿鱼也得叫个车回家啊。给丫挣钱丫不要,也就能给丫当司机了。”贺萧说得有些愤慨。
“您可甭介,这不是世道不好么,三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”
“操,一直是好汉,只不过虎落平阳被犬欺,哈哈。”
一来一往,车里都是两个大老爷们逗贫的声音,贺萧摇下窗户,想起这是春天了。现在北京也刮不起沙尘暴,但儿时漫天飞舞的杨柳絮也同时不见了,地球够憋屈的,大概会跟他一起爆炸吧。
给母亲去了个电话,电话那头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:“那就去读书吧,我跟你爸一直觉得你应该去读个硕士,你看人家田容跟你一起清华毕业,现在博士都快读完了,多有出息。”
“得了,我不是读书的料,让我读书还不如杀了我算呢,没这耐心。”贺萧心里开始烦躁,怎么老是提这事儿。
那边火气也上来了:“噢,怎么那么多人都能读,就你读不了啊?你工作,你这工作一点意义都没有,混也混不下去……”
“诶你烦不烦,你儿子就是无能行了吧,你说的是别人的生活,我没义务把别人的人生再过一遍。”他也控制不了自己,冷静不下来,车窗外的风往耳朵里灌,吵得他都听不见自己的话语,再说下去只会又把关系闹僵,父母惹不起还哄不起么,“行了,有点吵,听不见你说什么。小穆刚出差回来,周末我陪她,就不回家了,拜拜。”
赶紧挂了电话,好像再说一秒钟就要窒息身亡了,肺里面每一个气泡都肿胀得发疼,不自觉拽开领带,抚上自己的喉咙,还好,并没有什么东西勒着。
眼看着就快到天通苑,贺萧又觉得不应该回家闷着,好歹他现在没的卖命了:“师傅,转去德内吧,先去看看女朋友。”
“得嘞,还是温柔乡能解闷儿呦。”司机的语气暧昧。贺萧突然懒得说话了,揉了揉眉心往后背靠去,他并不太想看见自己的高中。
他也没有特别喜欢穆华,不过进了四中以后,初中的哥们都陆续找了媳妇,他也不甘落后,挑挑同班的女孩,筛拣出这么一个。这其中当然也有年畅的建议。
年畅和他是从一个班里考进四中的,高中并不同班,但年畅和穆华是室友。那天在礼堂里,什么活动开会,年畅坐在老旧的木头折叠椅子上,仰头看着他,午后的阳光正好从墙顶上的那排小窗户跳进来,照在年畅脸上,让他觉得年畅的话仿佛是不可动摇的神旨。
“诶,贺萧,你觉得穆华怎么样啊?人家可追你呢,你倒连个表示都没有。”
“她追我?我怎么不知道,就是比较熟吧。”
“追你都不知道,早知道初中应该追追你,也算爱的教育,哈哈。”他好像看不见年畅在笑,就记得她脸上一团白绒绒的光。
贺萧和年畅初中的时候被同学起过哄,偏偏贺萧确实心里有鬼,但年轻气盛总是好面子,两个人后来开始避嫌,有两年没怎么讲过话。上高中以后算是冰释前嫌,唇枪舌战总是很多,有时候互相讽刺,有时候暧昧两句,没个正经,像年畅说的,“就不能和平相处”。
年畅跟他说过以后,他和穆华就算是顺利发展吧,早恋的年岁,神秘感夹杂着新鲜,就一直好到了高中毕业。穆华的大学是在香港念的,临别送行的时候哄了她半天,但结局就和所有长距离的恋爱一样,他觉得挺自然的。在大学认识了上海小姑娘田容,拖了几年,到现在也没个结果,也就算红颜知己。后来毕业回京,又见着穆华,到底觉得人家包容性强,挺适合娶来当老婆,一来二去又复合了。
当然心境早已不同,历练了几年,花言巧语对贺萧来说早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,有时候看看穆华对他死心塌地的模样都觉得好笑。比如穆华说为了纪念他们最初的时光,特地在德内大街租了房子;比如她会在纪念日的时候送他一本分手时她写给他的诗集。
但好像即使是现在,穆华对他来说还是筛子里面剩下的那个。不过骗一骗,也就是一辈子了。
车已经沿着平安大道行至北大医院,其实就算穆华租了这里的房子,整条德内大街也是翻修一新,早已经没有记忆中的影子了。
穆华曾经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,两个人下午下课以后到后海边聊天。那时德内大街很窄,两条车道宽,也没有划出自行车和行人的专用道,破自行车载着两人在车队里七扭八歪地穿梭着。穆华扑在他后背,一直嚷嚷。她一直这样,好像嘴一咧开就是快乐。两旁的平房飞快地后退,偶尔能见着有枝丫破墙而出,到后来走的次数多了,甚至哪家的墙头有草都已经烂熟于心。每次到了后海,穆华都迫不及待地跳下车座,那铁架子坐着也确实不舒服。贺萧就把车就随便往路边一靠,带着穆华翻过栏杆,坐在湖岸雕砌工整的石头上,聊聊便是一个放松的午后。穆华后来说她记忆里的后海是永远阳光明媚的,逆着光看贺萧,发尖渲染着温柔的金黄,那么温暖,赶走了她应有的忧愁雨季。贺萧却觉得后海潮湿粘腻,可能是骑着车弄得一身汗,偶尔夏风拂过,穆华的发丝会飘到他脸上,抓也抓不下来。
穆华开门的时候脸色憔悴,仍然掩不住眼睛里的欣喜:“贺萧,我正想着要不要给你打电话,你就来了。”
贺萧搂着穆华进屋,心不在焉地应着:“找我做什么?”
“我昨天回来觉得好累,早上发烧了,现在浑身都酸疼的。公司又说什么让大家准备无薪休假,烦死了。”穆华的嘴唇发白,却一直动着,速度很快,“贺萧,你说这过得是什么日子啊?”
“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了,要不要吃点东西?”贺萧想自己还不如不来,暗自后悔着,但应付的词语却是不经大脑就出了口。
“不吃,没胃口,哎呀,烦死了烦死了。”穆华仍然在烦恼,也不知道是烦生病还是烦工作。
贺萧送穆华回卧室躺下,坐在床边,抚着她的手,因为生病,手指有点浮肿。贺萧觉得有什么一直从心脏往嘴里冲,他只好转了视线去看窗外。那些平房早就没有了,德内现在是好几条车道宽的大马路,两边板楼一栋挨着一栋,窗外不过是另一个窗子,黑洞洞的,像要把人的精神都吸进去。
他得离开这儿,尤其是穆华又靠过来圈着他的手臂,让他想起来小时候课文里鲁迅说的美女蛇:“我只是跑客户顺路过来看看,你乖乖休息,我明天再来照顾你。”
穆华的手攥得紧了一些,但也只是一瞬间的事,她一直说自己善解人意。贺萧有点残忍地看那只惨白的手挣扎,慢慢缩回被子里,好像白骨精被打出了原形,灰溜溜地钻回了山洞,他俯身,嘴唇碰到穆华的额头,她嘴咧了一下,倒很勉强。
他忽然觉得谁都活得很勉强。在心里叹了口气,阖上门走了。
还能去哪呢,贺萧坐在这天的第三辆出租车里,就让司机绕着二环转,路两旁都是一样的,走一会上一个桥,坐在车里看桥也都是一样。本来这里一圈都应该是城墙,还有城楼门,各不相同:“都他妈让那群混蛋拆光了。”贺萧忍不住自言自语,司机是个秃顶,从后视镜里很快瞥了他一眼。
漫无目的地转了一下午,丢给人家几百块钱的车费,六点,也是下班时间了,贺萧这才甘心回了家。
看到一封田容的邮件:
“贺:
你生日快到了。我决定给你买条领带,放假时候带回来。为了避免重复,现呼唤你把你已经有的颜色式样发过来给我!”
贺萧突然觉得一阵脆弱,他很想见田容,哪怕只是见面后朋友间的拥抱也好。他大学时候追了田容很久,但田容心不在国内,到最后也就落得个朋友的关系。红颜知己吧,贺萧固执地拿这个词定义田容,以此证明自己也是个值得羡慕的男人。
上了Skype,田容在,贺萧反而紧张了,他也不想让田容觉得自己还迷她,但很想她飞回上海的时候在北京转机。哪怕停留个两小时,吃顿饭。田容的电话倒是打来了,手指比大脑反应灵敏,先按了接听键。
“今天这么早下班?我的邮件收到没有?”田容的声音轻快,但经过数字化的处理到底不如记忆里亲切。
“嗯,为什么突然要买领带啊?我不缺领带的。”也许不要礼物就能要求她见一面了吧,贺萧心里有了主意。
“诶这个由我决定,花钱我开心。”田容一贯的口吻,只是话题忽然变了,“贺萧,我问你个问题啊,如果一个男生走路搂着女生,是不是有喜欢的意思啊?”
贺萧发现自己原来想的话接不上了,田容在镜头那边一只手捂在自己的肩上忙活:“不是哥们儿的那种勾着脖子哦,是这样子搭在肩上,你看得见吧,这样是偏向于男女之间的模式,对吧。”
贺萧嗯了几次,田容那边大概没有听到,一直问是不是,贺萧最后把“是”字拖了老长的音,才看见田容笑了出来:“那么半天才回答……”
直到两人挂了电话,贺萧都没把想见田容的事情说出来,主要铺垫好的主题总是被田容拐走,而他也并不如大学时代那样毫无顾忌了。他觉得很累,耳朵一只嗡鸣,鞋也没脱就倒在了床上,看着天花板,上面连只虫子蜘蛛都没有。
其实他觉得生日卡片就够了,“生日快乐”四个字的背后无非是人情往来,早就没有学生时代的单纯了。
年畅也送过他生日卡片,那已经是十三四岁的时候了。他记得年畅是他同桌,个子高挑,皮肤很白,显得眉眼格外清晰。放学回家两人有一段同路,有说有笑地一起骑车放学。他那一年很喜欢年畅,也说不清楚是因为自己一定要装个人在心里,还是真的就是喜欢。年畅在他面前很酷,话不多,但偶尔走路却会动作不协调。年畅的生日卡片写得中规中矩,都是字面上的话,只附注了一串数字:564335,到现在他都记得,因为他着实猜过一阵子,问年畅,她说没什么。班里的男生很少,他跟年畅的八卦很快就在女生堆里传开了,后来两个人的座位调开了,话也少了,放学也就各走各的,幸亏北京城的路都是井字模样,换一条路也不会有什么影响。
贺萧躺在床上又想起来那串数字,冷不丁决定起身去查查看,动作有点慌张,仿佛什么天大的秘密要揭开了一样。百度上第一条就有,甚至不用点进具体的页面:“无聊时想想我”。
年畅的脸忽然跳了出来,伴着她慢悠悠的话语。他想起两个人避嫌装成陌生人的那两年,想起初中毕业以后的针锋相对。直到现在年畅都偶尔会在facebook上面嘲讽他一句。
“搞这么含蓄!”贺萧愤愤不平地念叨了一句,好像如果他猜出了谜底,就会有不一样的故事发生,他会去跟年畅表白,再之后也不会有穆华,他会在年畅的感染下跑去美国包个金回来,那么今天的一切也都会不一样。他越想越觉得有些气年畅,同时他又想去告诉田容,但他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,他好像永远无法顺利对田容说出来他预备的话。
贺萧打开酒柜,也不管什么牌子类型了,打开直接对着瓶嘴喝,越贵的喝得越急。凉滑的液体从嘴角溢出来,顺着脖颈流到衣服里,好像又回到后海的那些和穆华在一起的午后,潮湿又堆满尘埃。窗外灯火渐渐多了起来,贺萧也数不清楚,慢慢的就好像看着一团火在转动,余光瞥着是顺时针,定睛一瞧又变成了逆时针,他觉得有趣,咯咯笑了起来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喝酒,或者原因一直都在,只是以前没有时间放纵。也不需要什么音响效果了,他耳朵里一直是咚咚的节奏声,愈来愈强,他甚至忍不住要跟着摇头晃脑起来。
折腾了一会儿贺萧变觉得热了,起身想去开空调,走了两步都晕乎乎的。原来醉酒跟女人高潮一样,和内心的意愿程度成正比的,到最后他也分不出来是真的醉了还是让自己相信自己醉了。反正是有些恶心,趴在马桶边上,等着胃里的酸水往上冒,嘴里唾液越来越多,吞咽的能力都已经失去。贺萧觉得这是多神奇的一件事,人不仅控制不了其他事情,连自己的身体都管不住,残羹碎渣一股脑从喉头喷出来,他都不需要用力,只要等着胃部自主的阵阵收缩就好。偶尔有没有嚼烂的东西,他更加恶心,也想不起自己前一天都吃了什么,怎么还是消化不掉。
这样吐了两三拨,贺萧坐在地上愣了会神,才狼狈地站起来,颤颤悠悠,拿出杯子漱口,胃酸如火一般灼烧着嗓子,呼吸也不顺畅。洗手间里没有开灯,微弱的光是窗外映进来的,他抬起头看着洗漱镜里的自己,也是一片模糊地在动,往左,往右,微弱的起伏是他喘气的节奏。他 又觉得镜子里好像不是他自己,是一个女人,但看不真切,只有大大的黑眼圈那么明显,好像刚刚出土的干尸,他在新闻里见过的。不是穆华,不是年畅,也不是田容,又或许是,只不过他不认得了。
电话铃在响,划破他的精神,卫生间里轰地一亮。他胡乱冲了下手从裤兜里摸出手机,似乎连按下通话键的力气都没有,要咬牙切齿才能办到。
“喂,贺萧,你逍遥呐?公司聚餐,我就不去投奔你了,你别太放纵啊, 哈哈。”电话里传来的声音突然盖过了耳朵里的咚咚声,如爆炸一般充满整个空间,他一点都不想听见,他还在看镜子里的女人到底是谁。
“你谁啊?”贺萧问着。
“你丫没事儿吧,我孙奇啊。”手里的机器在发出声音。
贺萧有些愣,女人的脸一会儿变一下,他只是觉得手里的东西让他无法专心辨认,回声一层一层满屋子都是,他本能地对着手机吼了一句,然后摔进马桶里:
“操你大爷,滚。”